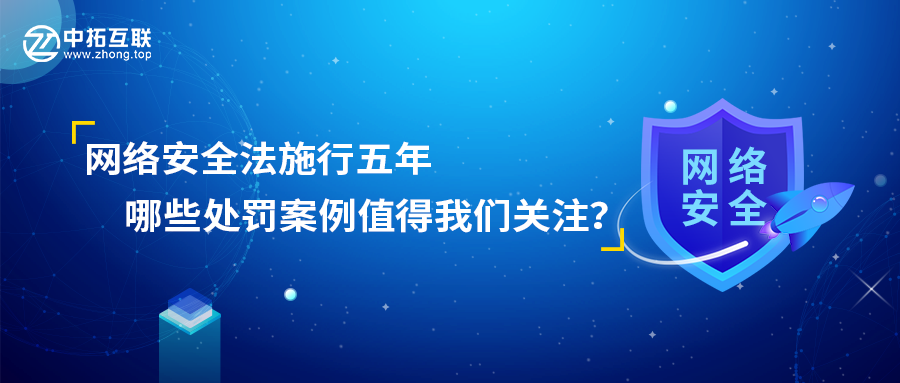新冠疫情让蛰伏了几十年的纳米载体技术“一朝颠覆”,成为大热的产业领域。

这样的“颠覆性技术”如何才能出现?怎样才能发展?全国两会期间,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不同领域的全国政协委员。
“从基础研究到真正的大规模应用常常需要较长时间,例如,mRNA和脂质体的基础科学发现都是在20世纪60年代,到脂质体纳米载体的mRNA疫苗问世,经过了整整60年。”提到颠覆性技术,全国政协委员、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主任赵宇亮院士表示,一项技术能不能服务于社会,实现颠覆,首先取决于基础研究的科学发现,而后是技术能不能发展,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。
“基础科学的前沿突破有望诞生颠覆性技术,量子技术就是很好的例子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吴季表示,要孵化颠覆性技术,需要有气度、有信心在基础研究方面做出别人没做出过的东西。
基础研究需要有组织
从0到1的基础科学研究是颠覆性技术的源头和“储备库”。
“像牛顿那种理论突破式的颠覆性发现现在已经很少了,如今要实现基础研究的突破需要借助先进仪器设备,一类是地面上的大科学装置,一类是空间中的科学卫星。”吴季说,20世纪90年代以来,一半以上物理类基础研究的突破来自这一类研究。
我国在部分领域正走在前列,例如,“中国天眼”FAST、量子科学实验卫星“墨子号”、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“悟空号”、散列中子源等。其中量子通信技术已经在实际应用中落地。
“这类基础研究首先要有自己的装置,其次需要可持续发展的支持。”吴季说,在“墨子号”等项目上已经走出了成功的范式,我国应该进一步利用国家体制的优势,开展有组织的、定向的重大科学基础研究。
然而,在科学卫星的评审会上,吴季仍会有很多不舍。“科学家们的建议很多,但得到的支持还不够,按照每年只打1颗科学卫星的规划,难以满足科学探索的需求。”吴季说,作为评审专家很难选择,很多开拓性的项目遗憾落选。
“国家应该在空间科学领域设立专项,增加科学卫星的发射机会。”吴季说,近年来,卫星的发射成本在降低,基础研究应抓住时机,逐渐从跟跑、并跑转向领跑。
技术精进需要有耐心
颠覆性技术并不像它字面上看起来那么突然。
“它的诞生不是一日之功。”赵宇亮举例说,能做载体的脂质体颗粒很早就有,但一直在微米级别,达不到疫苗载体可用的纳米级;经过几十年的发展,人们才把它变成质量可控的纳米脂质体,但又一直难以做到可控和大小均匀;直到人们发明了“芯片微流控技术”控制纳米颗粒的生成,才实现了质量可控的大规模制备。
很多颠覆性技术的发展路径都是这样“一波三折”。“实际上科学发现以后,在实际应用阶段需要解决很多技术性问题,也会面临更多新出现的问题,走向成熟需要时间。”赵宇亮说,所以,社会各界特别是领导层、管理层需要提高对基础研究和原创成果的时间忍耐度。国家对基础科学研究的强力支持不能忽冷忽热、对前沿方向的探索也不能断断续续,国家对从基础研究到实际应用间的科技创新全链条,应有完整布局和支持,才能“孵化”颠覆性技术。
去年《科学》发布的全世界最前沿的125个科学问题被认为是颠覆性技术的“任务单”,它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第一条就提出了:可注射的抗病纳米机器人会成为现实吗?
“智能化的纳米机器人是纳米载体的下一个目标。”赵宇亮说,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团队目前处于该领域研究的领先地位,可以将DNA分子编织成“高铁车厢”载着药物分子进入体内,在血液循环系统中是球状,遇到肿瘤时自动“变形”成尖刀状钻入肿瘤内部,有点像“变形金刚”,能解决肿瘤组织致密、难以攻破的问题。
“有了可注射纳米机器人,将来的外科手术也可能被取代。”赵宇亮说,颠覆性技术不可能靠单一领域的科学家来完成,不同学科之间能够实现高水平的学科交叉是关键。例如,我国在纳米机器人的基础研究上走在前列,但要落地应用需要材料科学家、化学家、微纳工程师、药学家、临床医生、生物信息学家等共同努力,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智能化、更广泛的应用。( 张佳星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