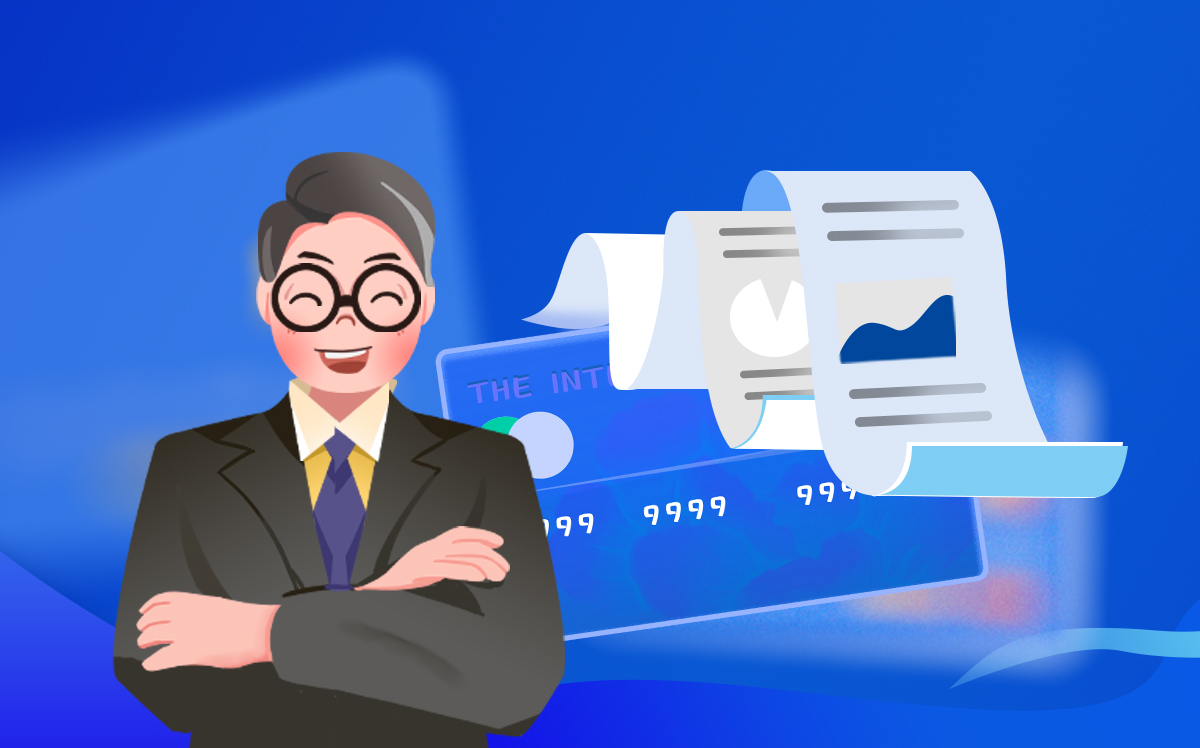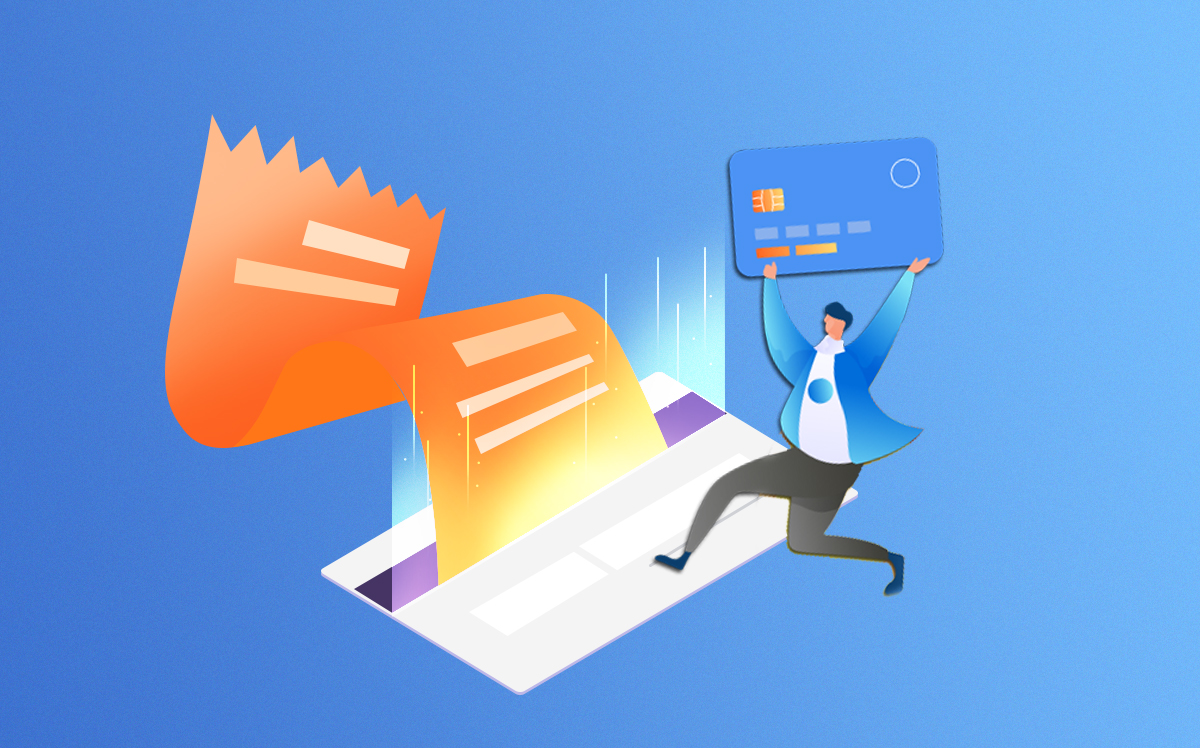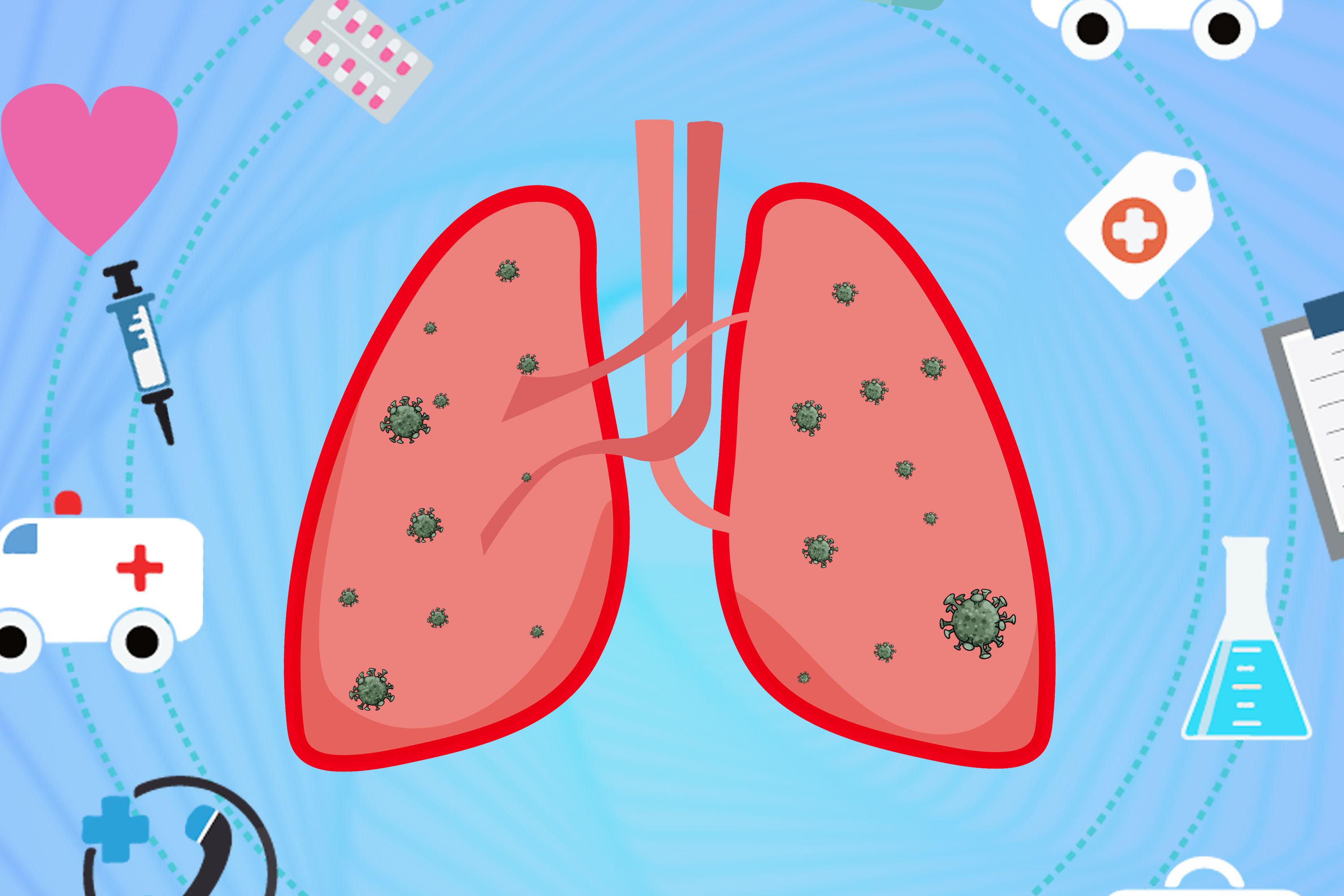信用不仅催生了契约,推动了市场,还将人际关系从简单的人际互动推向更高层面的社会联合,实现了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世纪跨越。

民法典第1029条就民事主体的信用评价规定了查询、更正和删除三种权利:当民事主体发现有不当信用评价的,可以提出异议并且请求更正或删除。如此规范,无疑证明了信用评价对民事主体的重要影响力。特别是网络时代,无论是官方的失信平台曝光,抑或是自媒体的实名投诉,都可能诱发个体或企业的“社会性死亡”。这也印证了孔子“自古皆有死,民无信不立”的经典命题:生死是事实判断,信义则属于价值判断,一个人是守信还是失信,直接会影响到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。
信用与生命价值、人格尊严、经济利益发生直接关联,这在中西文化中具有高度一致性。西塞罗曾以反诘语气直言:“没有诚实,何来尊严?”中国自周秦以来,都以信用为治国齐家之本,即便处于社会底层的百姓也可通过形象的比喻教育子孙:“火心要空,人心要实。”——火心空则易燃节能,人心实则有信多友。
为什么说人无信不立?第一,信用是个体立身的基本要素。传统法律为维护诚信,西方曾出现过耐克逊之债,债权人有权拘禁、买卖甚至杀死失信的债务人,中国也有役身折酬,通过身体强制惩戒失信者。即便近现代废除了对人身的强制,但污点记载、失信记录不仅危及个人信誉,同样也会危及人格尊严和行动自由。
第二,信用是人际互动的基本规则。人类之所以能摆脱狮群猴群的丛林法则,其最大的发明就是契约,开启了有机的社会团结之路。契约的最终目的可能是利益的互换,但其起点绝对源自对相对方的人身信任和对契约条款的遵从践行。缘乎此,传统中国将“信义”并列,守信成为最低的道德标准,但其结果就会催生至高无上的“义”。无论是蓬门荜户之间的纸质草约,还是皇家与功臣之间的金书铁券,最高的“义”永远大于、先于现实的“利”。
第三,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。按照博弈论逻辑,市场博弈本身就是利益博弈,信息是否对称决定了参与人的行为方式和战略决策。如果“信息不对称”,出现信用风险,就会陷入“不完全信息博弈”,导致一方做出违背真意的决策并最终受损。对此,法律所能做的仅仅是要求信息披露,为博弈双方提供平等的选择权、谈判权;而市场则可以利益打败利益:让失信者的失信成本远大于失信收益。如此,再卑鄙的小人也会被动成为守信君子。即便他追求的是纯利益,但客观上维护了可贵的道德。这是市场的魅力,也是市场的魔力。
第四,信用是社会联合的基本动力。信用不仅催生了契约,推动了市场,还将人际关系从简单的人际互动推向更高层面的社会联合,实现了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世纪跨越。传统中国为什么难以逾越家庭伦理?因为家庭的身份认同与人身信用具有高度同质性同态性。即便产生了超血缘的社会联合体,也会策略性地通过拟制血缘强化彼此间的人身信用。这种拟家化特征不仅体现于传统的行会会馆之中,也隐含于现代化的公司企业之间。
概言之,信用是道德诉求的制度化。“人无信不立”所谓的“立”,无非指向的是信用的三维立体动能:体现最低道德限度,产出最优制度效用,营造最好人际环境。(刘云生)